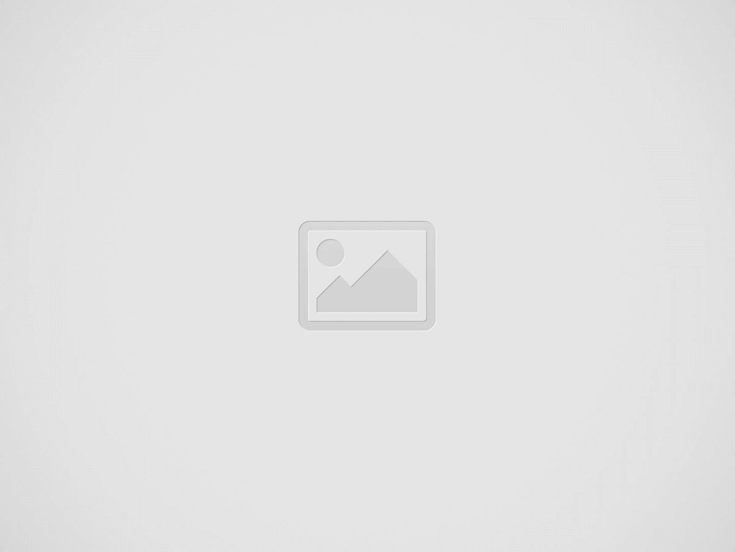在過去的六週裡,Gamekult 與 Libération 的 Erwan Cario 和 Marius Chapuis 合作,並接到電玩工人工會要求證人的通知,對法國的電玩培訓及其功能失調產生了密切的興趣。這項調查是基於對學生或前學生、在這些培訓課程中任教或曾任教的教師的41 次直接訪談,以及大約50 份書面證詞以及與該領域各利益相關者(工會、協會等)的討論。為了保護其作者,大多數證詞都已匿名。面對在我們收集證詞和文件時所揭露的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也決定分三部分公佈調查結果。
Valentin Cebo 與 Virgile Rasera 夫婦
這項調查的第一個主題是我們開始對電子遊戲學校感興趣的點:加班,或者更確切地說,有利於其合法化和內部化的條件,作為「行業」未來工人不可避免的約束。因此,我們意識到,長期超負荷工作並不是某些工作室的唯一問題,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學校中找到根源。騷擾、性別暴力和性暴力以及某些歧視性言論和行為的問題也很常見;這將是我們第二篇文章的主題。最後,根據我們的採訪,我們不能滿足於對所有這些系統性功能障礙進行簡單的清單,而不將它們與這些大型私立學校的結構性破壞以及它們建立和繁殖的經濟原因聯繫起來。
在開始我們的第一部分並詳細討論工作節奏和加班的學術合法性問題之前,對我們來說,作為序言,起草一份法國領土上視頻遊戲職業培訓供應的清單似乎很重要。足以讓你理解它是如何表達的以及它的缺陷是如何出現的。
法國的電子遊戲培訓
近年來,許多「電子遊戲學校」在法國蓬勃發展,這些學校在一般為期三到五年的課程框架內培養未來的電子遊戲男女。國家電玩聯盟的正式名稱是“教育組織”,這個名稱匯集了提供視頻遊戲創作相關培訓的大學、某些數位藝術學校,或者更明顯的是視頻遊戲學校 - 我們在這裡感興趣的專業機構。

據法國統計局稱,法國有 87 至 133 個此類組織SNJV 官方晴雨表,其中包括 SNJV(國家視頻遊戲聯盟,代表法國該行業的公司和專業人士)建立的視頻遊戲學校網絡中的 12 所學校以及“突顯培訓品質和優質教育服務,適應活動部門的要求」。直到最近幾個月,學校的創始人在加入 REJV 之前就已經制定了標準清單。自 2021 年以來,SNJV 董事會研究了這些文件,並表示它提供了“非常客觀的閱讀」。具體而言,該網絡列出了該領域最負盛名的學校,並構成了排名費加羅學生例如,家長和未來的學生可以用來選擇課程的來源。
這些學校大多是私立學校,如瓦朗謝訥的Rubika(匯集了電玩遊戲、動畫和設計三所學校Supinfogame、Supinfocom和ISD)、巴黎的ISART、LISAA、Bellecour和ICAN;他們的學費一般為每年6000歐元左右,最高可達9500歐元以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年利率會隨著課程的進行而增加,範圍從學士水平(Bac +3)到碩士學位(Bac +5),有多種可能性:國家涵蓋的文憑(在這種情況下)例如,公共培訓)、在國家專業認證目錄(RNCP,其作用是在全國範圍內使文憑合法化)註冊的文憑、來自不被國家認可的機構的文憑,和/或一定數量的 ECTS 學分可在歐洲不同的學校使用。

還有公共培訓課程,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昂古萊姆的國家遊戲和互動媒體學院 Cnam-Enjmin 提供的課程。作為電子遊戲學校網路中唯一的公共培訓,它構成了一個有點特殊的情況:那裡的學費每年略高於 300 歐元,並且該機構要求其考生具有 Bac +3 級或至少 3 級多年的專業環境經驗,為他們提供兩年學習後的碩士學位(RNCP 7級)。它是唯一一所在其宣傳冊中明確指出也為視頻遊戲和數位媒體領域的研究職業提供培訓的學校之一,特別是基於共同的學習核心、更專業的課程和研究介紹。
今天還有幾所大學提供數字藝術和視頻遊戲的許可證或碩士學位,IUT/DUT,其中包括視頻遊戲編程的介紹,甚至可能為視頻遊戲專業提供一年的專業許可證,就像以蒙彼利埃保羅瓦萊里大學為例。
這些培訓課程的內容
在法國,這些專門學校的培訓時間通常分為兩部分:學士部分,相當於學生畢業後獲得執照級別的三年,以及碩士部分,指定學習的第四年和第五年。不同學校的教學法和所有課程顯然有所不同,但我們仍然發現所有機構都有共同的指導方針。
學生被分為兩個甚至三個不同的類別:遊戲設計(GD),遊戲藝術(GA),有時還包括程式設計(如果學校提供這門課程)。 GD 學生將參加以下課程遊戲設計、藝術史、一般文化、趣味文化甚至關卡設計,而他們參加GA訓練的戰友將有更多面向傳統繪圖、3D、數位繪畫甚至角色設計。這些課程是習慣使用 Unity、Unreal Engine、3DS Max、Substance Painter 或 Maya 等工具的機會,這些工具現在在電玩產業的不同產業中經常使用。

一些學校還可以提供所有行業通用的核心課程,例如溝通課程、專案管理,甚至由不同的開發人員、藝術家或行業參與者直接與學生分享經驗的更多學術課程。後者與全職教授一起工作,但全職教授比外部演講者更為罕見。更多的理論課程也可以納入第一年,旨在向未來的學生教授基礎知識。遊戲設計師在處理電玩遊戲的設計之前,先了解棋盤遊戲的工作原理。然後,所提供的課程將在小組專案的框架內逐步付諸實踐。
在整個培訓過程中,協作工作也不斷增加,為學生在工作室或團隊中工作做好準備。因此,除了個人專案(寫作、繪畫或更傳統的評估)之外,學生還需要在專案框架內與不同部門合作,這可能需要一到幾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

創建原型,想像一個宇宙,進行演示或開發一個響應主題或給定限制的遊戲:練習和評估取決於科目和教師,但理論上允許學生接觸所有內容,以便沉浸式學習盡可能在專業環境中。這種小組工作的原則是 PFE 的基礎,PFE 是學習結束項目,通常佔用學生第四年和第五年的大部分時間。這些是學校可能在貿易展覽會、網站或宣傳冊上強調的項目,因為它們應該代表數年培訓的成果,並提升招募人員和電玩工作室所尋求的技能。此外,這些課程通常包括幾個月的實習,讓學生能夠在商界立足,並可以代表一種發展他們的通訊錄的方法。
從理論上講,這是大多數視頻遊戲培訓組織所提供的。但在談到這種在他們內部觀察到並被我們的證言廣泛記錄的著名「加班文化」之前,我們似乎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識。
任務授權的積累

«你沒有時間做校外的任何事。如果你創作音樂,你就停止播放音樂。如果你參加體育運動,你就會停止運動。你不做任何其他事»,Léa* 解釋道,她是 Supinfogame (Rubika) 的前學生,Supinfogame (Rubika) 是法國最負盛名的電子遊戲學校之一,位於瓦朗謝訥,從而指出了強加給學生的節奏的後果。必須指出的是,此類培訓的一年是圍繞著眾多個人或集體項目進行的:每週、每月或每年的工作,旨在將課堂上向學生提供的課程付諸實踐。 “第二年我就真正感受到了。第一年,老師們對我們很細心、體貼,但從第二年開始,我們就開始疏遠了,工作量開始增加。它是在渲染之後渲染的,不一定是超級有趣的東西,而且它代表了很多工作“,她繼續說。這些項目的範圍可以從編寫場景到設計符合特定標準或主題的小遊戲,包括要渲染的建模或繪圖。
在 Supinfogame 的前三年,理論課程相互銜接,涉及形成未來的不同主題遊戲設計師或者遊戲藝術家在創建視頻遊戲的所有階段。從藝術史到人體解剖學,透過電影構圖或具體案例的研究,邀請學生對所有專業保持好奇心和興趣,以促進未來的交流並盡可能多才多藝。

然而,第一年的重點是「基礎知識」:遊戲設計團隊棋盤遊戲的理論和設計,在玩視頻遊戲之前了解遊戲系統和機制的工作原理。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嘗試設計紙牌遊戲或棋盤遊戲的機會,並學習如何在管理時間表的同時在小組內分配任務。 “我們從來沒有老師給我們一個不合理的截止日期來做某事,它總是分散在幾週或幾個月內。然後我們就可以將其納入我們的日程安排中。»,Supinfogame 的本科生 Morgane* 保證。
她繼續說:「之後,有一些「有點混亂」的時刻,一般來說,這是學期結束的時候。所有預產期都在同一周。例如,如果我們必須在 1 月 31 日之前完成成績,那麼 1 月份的每週我們都會有一個繁重的項目需要提交,如果我們沒有領先一步,那就是大緊縮。徹夜難眠,從清晨工作到深夜,休息結束,我們不再玩電子遊戲,放鬆不再存在。如果組織良好,這種情況是可以避免的,但有時卻並非如此。»。
身為幾所學校的老師阿諾也向我們講述了效果圖的累積:「有一個問題是我經常遇到的,也是對成千上萬的老師來說的:你上課,你提出問題,卻沒有人回答。事實上,後來有學生來找我,告訴我,如果沒有人回應,那是因為他們正在利用我的課時間來完成另一堂課上到期的作業。有學生告訴我們:「有時間的時候,我們想怎麼組織就怎麼組織;有時間的時候,我們就怎麼組織;有時間的時候,我們就怎麼組織。當我們不再有時間時,我們會查看要求我們提供的第一個渲染圖,然後集中精力。»
因為這是你的項目

這些密集工作通常發生在學期末或「密集週」期間,即行業專業人士向學生「推銷」練習並在幾天的製作結束時對其進行評估的實際工作期間。 “在這幾周里,大家都知道我們會日以繼夜地工作以按時提交項目。它被接受,甚至受到一些老師的鼓勵»,告訴我們多納蒂安*。一個特殊的框架旨在幫助年輕人為這個行業做好準備,讓他們在關鍵時刻沉浸在接近工作室的工作條件中,但這促使他們把健康、休閒和幸福放在一邊,以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
對於 SNJV 的總代表 Julien Villedieu 來說,這個行業已經成熟,加班的做法現在只會成為一段糟糕的回憶:「我們不能高興的是,在培訓中,我們試圖給學生施加壓力,或者我們試圖讓他們相信這就是視頻遊戲製作公司的情況。幾年前,Crunch 曾在某些工作室中採用過,但這種做法仍然趨於消失」。他繼續說:「Crunch 是一種古老的方法,在我們的工作室中沒有立足之地,顯然它是一種「教導」、「灌輸」方法或其他任何方法(…)。以公司中存在的事實來證明有毒做法的合理性是在工業結構上扔燙手山芋,我不同意這一點。」。對 SNJV 來說,絕大多數學校並沒有犯下這種行為。

«當你要求學生組隊從頭開始玩三個月的遊戲,同時給他們上幾週的課程時,你不需要發表鼓勵加班的演講,你不能這樣做,如果你想最後交付一些東西你必須在空閒時間、晚上和週末完成。所以這是陰險的,因為我們沒有告訴您這種情況在行業中發生,但我們實際上為您做好了準備。»,ENJMIN 前學生 Corentin* 說道遊戲設計師十幾年了。
在這些緊張的工作期間,早上遇到整夜沒睡或晚上在學校度過的學生的情況並不少見。 “如果您是一年級學生並且週末不在 Serre [Serre Numérique,Rubika 學校校舍],您就知道您將無法獲得分數»,Laetitia* 說。包括 Rubika 在內的許多學校也會在晚上和週末開放校舍供學生使用,以便他們希望聚會或使用學校的電腦設備。這實際上允許家裡裝備最差的學生使用學校的許可證和軟體來工作,但進一步模糊了生活空間和工作場所之間的(本來就很好的)界線。
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魯比卡管理層否認晚上開放營業場所:“校舍依照教育部的指示開放,即下午 6:30 以及週末(註冊後下午 1:00 至下午 6:30),應學生的要求開放。在 Rubika,場地的無障礙性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學生需要使用高效能硬體、特定軟體(特別是圖形軟體)以及良好的網路連線。»

«通常,在第四年,我們有一位教育總監,他在下午 5 點左右下課後走進房間,他對那些沒有做個人專案的學生大喊大叫。但另一方面,我們在凌晨 1 點到 7 點之間被拒絕進入溫室。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措施,但我們已經這樣做了很長時間並這樣操作,我們發現我們正在佔用我們的工作時間。»,魯比卡大學的前學生愛德華說。應該指出的是,除了課程、一次性項目、小組作業和密集週外,我們還鼓勵學生「研究自己的作品集」並參加課外項目,以獲得更多經驗和遊戲,以在簡歷中展示。 “第二年我真的很震驚地發現我周圍的每個人都沉迷於工作。我想知道是我太奇怪了,還是其他人太著迷了。當我們與管理階層談論這個問題時,他們鼓勵我們去工作,去做遊戲即興創作,做原型,去研究我們的作品集。每個人始終處於相同的心態»,莉亞解釋。
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我們做了很多遊戲即興表演,整個週末我們都沒有睡覺,我們吃了披薩。後來我們意識到這是不可持續的,這不是一個健康的步伐。
Léa*,Rubika 前學生
因此,學生需要每天上課幾個小時,同時完成學校專案和個人專案。 “我們看到Supinfocom(Rubika集團的動畫學校)的學生在深夜做專案時睡在報告廳裡»,四年前參加該機構的 Xavier* 回憶道。 Martin* 是 Rubika 的前學生,此後教授了多門課程,他指出:「學校舉辦了遊戲活動,並鼓勵學生週末來學校參加並展示下週的遊戲。這並不等於減輕後面的渲染效果。這是添加到其餘部分的。他們不是強制性的,但事實上這是很反常的:我們告訴學生我們將舉辦一場遊戲即興表演,這太酷了,因為他們要從頭到尾製作一個遊戲,所以顯然學生們,他們懷著善意去那裡。他們從週五晚上到週日晚上在那裡度過週末,精疲力竭,週一早上回到課堂並有其他作業要做。»
在培訓的頭幾年,學生的專業化問題也出現了,他們被告知必須「接觸一切以更好地了解不同行業並與他們更好地溝通」。雖然充分了解培訓課程可能缺乏專門針對更具體學科的課程或部分,例如像素藝術, 這角色設計或著色器。因此,這項工作必須經常在家完成,正如愛德華*向我們解釋的那樣:“我到達後,我離開了學士學位,我對 3D 沒有任何特殊的知識,所以我至少能夠學習基礎知識。但到了第三年之後,課程就不再那麼重要了,尤其是我的專業課程已經不多了。我想一年大概有三個。於是,我就訓練了自己。這就是這些訓練課程的問題所在,我們說它們是專業的,但聽起來有點像「包羅萬象的課程」。你發現自己的背景有點混蛋,並不真正讓你知道如何做某件事,而機構希望你訓練自己。但這種自我訓練的問題是,在學校期間無法完成。你已經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愛德華繼續說:「你每天花8個小時在課堂上,你還有作業要提交,除此之外你還有額外的作業,因為你必須找到你的路,找到你的工作,並且你必須擅長它。但這不是學校允許你做的事。她認為你可以在空閒時間做這件事。這推動了加班的正常化……回想起來,我今天的行為方式可能是完全瘋狂的。我們度過了密集的幾週,期間我在 72 小時內睡了 4 個小時,實際上,在裡面,我發現它很時尚。我對自己說,這太好了,我付出了我所擁有的一切來讓一個專案變得很酷,當時,感覺就像你正在盡你所能」。這也是在提交日期或密集週之前的緊張節奏和工作高峰的真正危險之一:加班在學生的頭腦中已經制度化,每個人都必須應對它。
在學校方面,我們經常用學生在確定專案範圍時的過度熱情和缺乏清醒來解釋工作量過大:“我們試圖降低學生的野心,特別是在學習結束專案期間。»,巴黎 ISART 副主任 Karin Houpillat 保證。 “我們總是要求他們減少時間,告訴他們最好打 10 分鐘而不是 40 分鐘。»

同一所學校負責商務關係的 Jean-Philippe Ourry 也有同樣的觀點:「但確實,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細微差別,對於熱情的學生來說,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可能意義不大。這就是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的困難所在。» 3Axes 管理層的同樣故事:“當我們發現自己陷入困境時,這是因為我們的組織不善,我們沒有很好地平衡項目,沒有很好地平衡需求。因此,我們確保他們承擔的專案相對於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團隊人數是可行的。學生總是眼大手大,當一個團隊只有五個人時,他們就想做大事»,學校校長尼古拉斯·勒普雷特 (Nicolas Leprêtre) 說。
團結、競爭、逆境
«要嘛你堅持,要嘛你停下來»,愛德華*吐露。在二十到三十名學生的班級裡,我們交流很多。互助和知識分享是電子遊戲學校教學的兩大支柱,也是許多學生所稱讚的特質。 “我們遇到充滿熱情的人,像我們這樣的人,我們分享提高生產力和互相幫助的技巧。顯然,我在培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能夠召開的會議»,魯比卡學院的學生路易絲說。 “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我們齊心協力,確保事情盡可能順利進行。」。學生可以互相鼓勵、分享技巧或溝通技巧。 “我們會在課後在某某的公寓見面,討論專案並了解進度情況,或者我們會去學校旁邊的酒吧討論課程。」。許多人談論從學校開始的真正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或者對某些人來說,與以前的同學創立了一個獨立工作室。

這種互助對於相處融洽的學生來說往往是有益的,但在容易感受到壓力的情況下,近距離和頻繁的合作有時會損害團隊氛圍。 “我們直接辨識哪些元素比其他元素更強,每個人都想與它們組成一個群體。每個人都想與班上最有才華的人成為朋友,與他們成為一個團隊。結果,它在班級中形成了群體:那些與最強者水平不同的人感到被極度排斥。沒有人想要它們,它創造了真正的泡沫», 告訴我們 Léa,她是 Rubika 的前學生。 “分歧開始出現,壓力、疲勞和偏執進一步加劇了分歧。我們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或那個學生不想和我們在一起,“他不喜歡我嗎”,“他認為我不夠堅強”或者什麼,我們開始想知道我們是否能找到一個小組學習結束專案的第五年。令人擔憂”,她說完了。
她繼續談論她與其他學生的關係:“當我試圖向他們保證一個項目或提交的內容時,我也與班上的人發生了很多爭執。我告訴他們要少擔心,不要壓力太大,多休息,如果他們沒有在背後對我大喊大叫,那就是臨界點了。人們告訴我,我沒有正確的態度,我不是一個可以這麼說的人,我永遠不會以這種心態找到工作。然而,這些都是我真正喜歡的人。今天我們再次談論這個話題,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是壓力讓我們這麼說的。我不是一個剛到學校就有壓力的人,甚至有些漫不經心。但看到我周圍所有這些人都給我帶來壓力,讓我感到壓力很大。所以我最終也做了同樣的事情,當人們工作做得不夠時,我最終對他們大喊大叫。»

因此,工作節奏、不斷提交的作業和學期末在某些班級中營造出一種令人焦慮的氛圍,疲勞和壓力加劇了緊張感。在電玩遊戲工作室中進行密集的加班工作常常會導致員工焦慮或疲勞,同時削弱他們的注意力和思維清晰度。他們求助於緊縮,因此疲勞,因此工作效果較差,因此必須更多地求助於緊縮 - 蛇咬尾巴的形象。我們在電子遊戲學校也發現了同樣的機制,一群學生必須在短時間內製作出多個效果圖,並且面臨來自教學團隊或身體老師的壓力。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遊戲藝術學生罹患肌腱炎的人數。太瘋狂了,要得肌腱炎,你真的必須畫很長時間,不改變姿勢。我見過很多人,我的朋友們因為工作太辛苦而得了肌腱炎。他們繼續在肌腱炎上畫畫或寫字。你想告訴這些人停下來,休息一下……不幸的是,這就是整個氛圍和我們給學生施加的壓力的症狀»,莉亞解釋。
“可以做得更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在營造良好氛圍的同時,分開事情、避免過度勞累。對許多人來說,工作負擔過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許多對話者向我們解釋說,他們在學習期間採取了加班加點的方式。學生的部分工作方法已經被學校專案和家庭作業壓得喘不過氣來,它經常被應用但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說受到質疑了。
很多時候,儘管有說法將加班的責任主要放在學生身上,但學校的教學團隊可能會意識到這些做法,有時甚至會鼓勵他們。 “我在魯比卡學習了一個學期,最後我的學生都跪下了。他們告訴我他們再也無法忍受了,甚至有人因為太累而不再來上課了。學生們向我報告說,魯比卡的教育主任參觀了班級,其中一個學生正在課桌上打瞌睡。他叫醒了她,並鼓勵學生“更好地管理他們的不眠之夜”»,教導魯比卡的馬丁*解釋。前學生朱爾斯*說:「學校非常清楚我們日以繼夜地為我們的遊戲而努力,他們在開放日強調了我們的工作並鼓勵我們更加努力。我們是最努力的學生,大家都稱讚我們,但內心深處卻互相傷害»。
當被問及工作超負荷問題以及為化解其後果而採取的措施時,魯比卡學校回應:“三年來,為了讓這些原型計畫得以實現,我們將獨立工作的時間增加到平均每月兩天,我們邀請他們參加「氧氣泡」課程,例如為藝術家提供雕塑或為遊戲設計師提供流行文化,我們隨時傾聽學生遇到的問題,我們每月召集推廣代表,儘早發現工作超負荷的潛在問題,並舉辦支持研討會,直至每月 6 至 8 小時。除了這些預防措施外,三年來,我們還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設立了一個心理傾聽小組,讓那些希望並感到需要表達自己的困難的人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因此,我們注意到,例如,在魯比卡,實施了一定數量的預防措施和系統,證明問題深深植根於教育的現實。然而,學校的責任可能超出了學生作業的唯一組織範圍,也涉及教學團隊舉行的正式或非正式討論。事實上,部分教學人員所表達的不遺餘力損害學生福祉的動機,有時是基於學生之間相當不正當的比較修辭過程。 Julien* 是巴黎最負盛名的學校之一的前遊戲藝術學生,他證明了這種做法:“課程的組織讓我可以兼職工作,有些老師以我的案例為例,告訴那些做不到的人可以找到工作並取得好成績,那為什麼他們不能呢?這讓我感到不舒服»。

當這些非正式的禁令沒有帶來預期的結果時,課程期間師生之間的評估將成為更正式、更具體的警告的契機:“在教育總監和教學團隊某些成員在場的季度訪談中,他們有時會告訴某人他處於困境,並向他施加壓力。學校裡有好幾個人經歷過職業倦怠,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當你把人們逼到極限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朱利安*繼續說。曾在魯比卡任教的教授馬丁*證實了這種經常使用學生內疚感和“充滿激情的職業”的修辭來證明這些禁令的合理性:“整個演講告訴學生:你必須工作,你在一所電子遊戲學校,你充滿熱情,當你充滿熱情時你就會工作。這些都是我學生時代也聽過的。當學生的生活和上課出席受到影響時,我們會責怪他們,讓他們因為無法控制節奏而感到內疚。»
有時,教師通常直接從學生那裡了解此類做法,並嘗試改進。有些幫助他們更好地管理日程,減少課程,讓他們在專案上取得應有的進展,有時花時間幫助課程或糾正遊戲中可能存在的錯誤。 “每次我上課時,我都會盡量讓學生意識到加班,並要求他們不要在課堂上過度勞累。»,e-artsup 老師 David* 解釋。 “當我看到他們陷入困境時,我甚至會花時間在晚上(有時是晚上 10 點或午夜左右)在 Discord 上回覆他們的訊息。這不是我的職責,但主要是在他們的預產期即將到來時幫助他們。»。
工作量問題其實是高等教育學校的普遍現象。從入學面試中,學生被告知他們正在努力學習。在數位設計和應用藝術學校中更是如此,熱情在學生的投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格雷戈里·薩拉切尼 (Grégory Saraceni),ICAN 總監
不幸的是,這是某些學校承認和鼓勵的製度化過度工作的另一面。學生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焦慮、負擔過重和擔心,他們會承受永久性的壓力(經濟、來自教學團隊或其他學生的壓力),這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或身體健康產生影響。許多人說他們在學習期間忽視或已經忽視了自己的健康,但實際上也不能這樣做。

«這麼說很傷心,但我有一些朋友在課程結束前就酗酒了。我們學校旁邊有一家酒吧,我們經常下課後在那裡聚會喝酒,但到了第三年年底,我們的朋友都是酗酒者,還有一些人患有憂鬱症。再說一次,我們很幸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通過了……我有朋友目前正在 ICAN 學習課程,不得不通過 Discord 通過答辯。當他們與遊戲設計的教育總監談論學生的健康和退學時,他告訴他們去參加體育運動或去看心理醫生,他說這不是他的問題»,ICAN 前學生 Bastien* 說。
氣喘吁籲
不幸的是,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聽到學生談論憂鬱症的情況並不少見,倦怠、疲勞或幾乎永久的壓力,這些壓力會在晚上伴隨他們回家,並伴隨他們整天上學。有些人每天晚上在酒吧見面討論工作,放學後在公寓裡繼續作業直到深夜,或者組織通宵,有時每週幾次,以免錯過平均重要項目的截止日期。事實上,學校並不是為學生的夜間工作制定框架的。
我們到處都在使用這個詞[倦怠]。倦怠並不是因為你在一個專案上工作了一個星期而感到疲勞。這是一種完全精疲力盡的狀態,失去對一切的品味和意義,這會導致放棄學習、失去熱情,並對這些職業感到厭惡。
Karin Houpillat,巴黎 ISART 副主任
在 3Axes 中,Pierre 教授的就是這種情況:「在 3Axes,導演親自安排了不眠之夜。他們向學生打開學校大門來完成專案。學生被邀請報名,但如果人數不足,校長會通知他們」。據管理層稱,這些夜晚將回應學生們的願望:「我們家的不眠之夜就是我們所謂的守夜 (...)» 學校校長尼古拉斯‧勒普雷特 (Nicolas Leprêtre) 說。 “一般來說,守夜活動是應學生的要求而安排的。說實話,這比什麼都讓我們煩惱,沒人願意晚上工作。我們已經第三年和第五年這樣做了,為的是那些需要在晚上多待一會兒的人。一般來說,這從來都不是好人的主動,而總是那些搞砸了的人的主動。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追趕這些學生»。

另一方面,這些都會受到監督,有利於營造更輕鬆的工作氛圍,該主任再次表示:「我喜歡它,裡面也有令人愉快的東西。因為現在是不同的時代,所以更友善一點,我們工作更隨意。不知何故,學生們喜歡它。這不是它的經典工作方式。之後,有些人熬夜,根本不工作。他們正在舉辦《任天堂明星大亂鬥》錦標賽。他們整個晚上都在玩視訊投影儀,根本不做任何事。有些人也利用守夜活動來做到這一點»。

更一般地說,「加班文化」這個詞在我們的討論中也經常出現。更糟的是,有些學生只有在經過幾年的訓練後,或是達到了極限時才意識到自己的疲勞狀態。 “即使事情進展不順利,你也注定要繼續下去,因為你為此付出了很多,或者因為其他學生都指望著你。我在四年級中期開始陷入憂鬱,並在五年級時完全處於最低谷。我還是不知道我是怎麼撐過來的»,愛德華*解釋。 “在我們五年級組,這幾乎被漫畫化了。有幾個人因為壓力而患上了慢性病,但小組中沒有人休息一周。更重要的是,我很沮喪。我們盡了一切努力堅持下去,但氣氛非常奇怪。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真正感覺到我們正在為發布我們想要製作的遊戲而奮鬥,而是像是我們在與自己作鬥爭,試圖最終發布一些東西。”,他說完了。
我有一個朋友,他靠吸食古柯鹼來度過夜晚的工作。我有幾個經歷過倦怠的人。另一位企圖自殺
Adrien*,ISART 前學生
ISART 的前學生 Adrien* 向我們證實,那裡的工作氣氛非常令人焦慮。在這種情況下,他告訴我們,例如,他的一位戰友在可卡因的影響下工作,以確保他的效果。 “我和這個學生以及另一個工作到很晚、下午 3 點到學校的學生之間存在一些問題。他們晚上就去上班了。我有錯,因為凌晨三點我無法修復錯誤。老師完全同意這些批評,並告訴我我還可以多做一點“,他繼續說道。 “我開始在學校喝咖啡。我每隔一天晚上就睡覺,我喝太多了。另外,從那時起我就不再喝咖啡了»,也告訴我們 Félix*,他是 Rubika 的前學生。
充耳不聞

透過與大約三十名這些課程的學生或前學生的交談,我們也看到了他們向教學團隊成員談論這件事的困難。一些經理或教師參與了 Rubika 的超負荷工作; ISART 的管理層向學生推薦他們工作“每天在家兩到三小時,除了上課,但不多了»;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在 ICAN,教育經理遊戲設計告訴他的學生去看心理學家,並拒絕承擔任何責任。然後我們了解損害的程度,以及一些學生在這些主題上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可能不願意的情況。電子遊戲學校內沒有系統地建立一個內部心理部門,讓學生可以分享他們的問題、疑慮和不安全感。
正如我們所報導的,Rubika 確實提供了熱線為其學生提供心理支持。但此類服務通常由機構外部的服務提供者提供。 ISART 似乎希望盡可能地將這種對處於心理困擾的學生的幫助內化:“學校生活團隊接受過心理健康急救訓練。這是一個為期兩天的培訓課程,可以幫助您發現倦怠的警告信號。目標是支持學生,使他們不會最終落入這樣的境地。» 卡琳‧霍皮拉特 (Karin Houpillat) 宣稱。她繼續說:「我們有一位精神科醫生陪同,他是 15-25 歲年齡層的專家,在這個特殊時期,學生正在全面發展並問自己很多問題。如果他們處於心理或其他痛苦狀態,它會引導我們採取後續行動。»
有一次,一位老師要求我們在晚上完成一個項目,隔天再進行。我們告訴他我們不會這樣做。起初他反應很糟糕,他告訴我們我們是愛哭鬼
Bastien*,ICAN 前學生
造成這種工作節奏的原因可能因學校而異,但在我們收集的大多數證詞中,教師和學生都向我們描述了一個缺乏協商和協調的教學機構。教師們常常自行其是,彼此之間很少交流,而是堆積起小組作業、個人專案和截止日期,直到學生報告作業過多。 “老師們彼此之間沒有真正的交流,也不一定知道我們在另一門課程中講過這個或那個。有一次,一位老師要求我們在晚上完成一個項目,隔天再進行。我們告訴他我們不會這樣做。起初,他反應很糟糕,他告訴我們我們是愛哭鬼。我們告訴他,我們今年花了很多錢,我們關心自己的健康,因為我們已經有其他專案了,我們設法改變了他的想法。他給了我們合理的時間來做這件事»,巴斯蒂安*解釋。

«在過去的兩三年裡,我觀察到學校正在努力了解工作量» 阿諾解釋道,他已在幾所主要學校任教多年。 “這些工具仍然很不完善,但想法是,每個部分,老師都會聲明他們要求學生在課外的額外時間,所有內容都計算在表格中,我們根據工作量是否可以承受分配顏色代碼或不」。例如,在 ISART 巴黎校區實施了一項舉措,但仍難以在教師中受歡迎:「我們有一個沒有被充分使用的工具,稱為“文本筆記本”,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班級的所有練習和當年的進度,以及每個學生在項目持續時間上必須允許的小時數或每天鍛煉身體(...)», 學校副主任 Karin Houpilart 解釋。 “當它變成紅色時,就意味著已經超過了每天2到3小時的標準。但確實,今天它是我們希望進一步開發的工具,因為它沒有得到足夠廣泛的使用或諮詢」。這些舉措仍處於起步階段,但似乎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圓圈已關閉
有些教師(個別情況下很少)也可以自願將學生推向極限,為他們進入工業世界做好準備。表達式“業界準備就緒»,描述準備被工作室聘用的學生,在我們的訪談中多次出現。例如,提到 Rubika 老師的案例,他“讓他的學生遭受他自己在工業界所遭受的痛苦”,或 New3dge 的校長,該學校是該領域最負盛名的學校之一,他建議疲憊不堪的學生“喝紅牛,因為這是他的最後一年»。

孤立地運作,旨在培訓高中畢業後進入職場的學生,圍繞這些原則闡述教學法的培訓課程對學生構成了真正的危險,他們一旦進入公司,就有陷入不健康模仿的風險。 Léa 也向我們透露:「畢業後,我在巴黎一家大工作室實習,並直接簽訂了定期合約。我在合約結束前就終止了合同,因為我已經精疲力盡了。 [...]從那時起,我就因憂鬱、焦慮而受到跟踪,我能夠了解學校發生的那些改變了我的事情»。
不幸的是,緊縮是電子遊戲世界中的現實。一個難以量化、難以定位、難以言語的現實。而是一個現實。如果說它是在培訓電玩工人的機構範圍內誕生的,那是不誠實的,因為它根植於媒體的 DNA 和某些工作室的製作方法中。但這些培訓課程在防止這種做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讓年輕人意識到過度工作的危險及其對他們可能產生的影響。如今,並非所有學校都承擔這一角色,但有些學校自願或不自願地參與了其製度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陰險的合法化可能會導致學生和未來的申請者重新考慮他們的職業選擇,如果他們意識到一旦學校大門關閉,現實與他們幻想的現實氛圍相去甚遠。如果學生晚上不睡覺,就很難向他們推銷夢想。
帕·維吉爾·拉塞拉和瓦倫丁·塞波
應目擊者的要求,名字已匿名
本文中的說明性圖片免版稅或直接來自官方學校網站。